[主要成就]
综述
刘辰翁的诗、词、文均寄托遥深、慷慨沉郁,深刻地反映了宋元易代之际的时代风貌和南宋遗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以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表现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对故国故土的眷恋。这在逃避现实、雕琢辞藻、充斥哀靡之音的宋末文坛是别具一格,值得充分肯定的。其诗气韵生动,无堆排涂饰之习,满怀沧桑之感与故国之思,具有尺幅千里之势。其词继承并发展了辛派词人的艺术传统,深刻地反映出了宋元易代之际的时代风貌和遗民心理,他的词风颇具特色,兼有豪放派的雄劲跌宕和婉约派的轻灵婉丽而自成一家。其文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宋末元初的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权材不平的心境和抑郁难宣的情绪使他的散文在造意谴词上流为奇怪磊落和迷离倘恍,在冗长拖沓的季宋文坛自成一家。
词
综述
刘辰翁的词属豪放风格,受苏东坡、辛弃疾的影响很深。辰翁的词对苏辛词派既是发扬又有创新,兼熔苏辛,扬其之长,使词风有苏辛之色,又不流于轻浮,形成自己独有的清空疏越之气。比之周邦彦一派,刘辰翁词不求矫揉造作而求真情实感,对元明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不无病呻吟的风格,在压抑个性的中世纪中国难能可贵。
题材
刘辰翁生前著述甚丰,但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的方面。他生逢宋、元易代之际,愤奸臣误国,痛宋室倾覆,满腔爱国热忱,时时寄于词中。在南宋末年的词人中,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反映得最为强烈,是辛弃疾一派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历代诗余》引张孟洁的话说:“刘辰翁作《宝鼎现》词,时为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自题曰:‘丁酉元夕’,亦义熙旧人(按:指陶渊明)只书甲子之意。”在刘辰翁的词中,凡属书甲子的词,都是暗示自己不承认元朝的统治,感怀时事、追念故国的作品。
他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就是这些感怀时事的爱国词。还在南宋亡国之前,他的某些词就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这首词是就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丧师败绩之事,直接抨击当时的腐败政治,对奸臣误国表示了极度的痛恨。尽管国事已不可收拾,他仍怀有报国杀敌的壮志,如《念奴娇·吾年如此》写道:“吾年如此,更梦里,犹作狼居胥意。”但他更多的爱国词则是写于宋亡之后,结合自己“乱后飘零独在”(《临江仙·将孙生日赋》)的身世,抒发对故国、故土的眷念与哀思。如作于德祐二年(1276年)暮春的《兰陵王·丙子送春》即是沉痛悼惜当年二月临安陷落,宗社沦亡的佳作。此词通篇采用象征手法,用“春去”暗喻南宋的灭亡。清人陈廷焯指出,此词“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白雨斋词话》)。由于写得字字血泪,沉痛感人,这首词常被后人视为刘辰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致厉鹗论词绝句有“送春苦调刘须溪”之句(《樊榭山房集》卷十二)。刘辰翁常常通过描写时令相代、景物变迁来寄寓亡国哀思。他在许多词中反复写元夕、端午、重阳,反复写伤春、送春,追和刘过的《唐多令 重过武昌》至七首之多,这些都不是伤春悲秋的滥调,而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眷恋故国故土的愁怀。如《永遇乐·璧月初晴》小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以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词中写李清照怀念“宣和旧日”,但尚及“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江南无路”、“春事谁主”的亡国之境了。因而此词较之李清照词,的确“悲苦过之”。又如《柳梢青·春感》,通过对故都风光的追恋和对眼前“笛里番腔,街头戏鼓”的憎恶,表达了与《兰陵王·丙子送春》一致的情感。
艺术手法
刘辰翁词不同于其他南宋遗民的一味掩抑低徊、凄凄切切,而是表现出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壮感情。他的思想境界比同辈为高,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喜用中锋突进的手法来表现自己奔放的感情,既不流于隐晦,也不假手雕琢,真挚自然,流畅生动,因而格外具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词能于沉痛悲苦中透发出激越豪壮之气,如《霜天晓角·和中斋九日》中的“老来无复味,老来无复泪”,《莺啼序·感怀》中的“我狂最喜高歌去,但高歌不是番腔底”,《忆秦娥·中斋上元客散感旧》中的“百年短短兴亡别,与君犹对当时月。当时月,照人烛泪,照人梅发”,《金缕曲·闻杜鹃》“少日都门路。听长亭、青山落日,不如归去。十八年间来往断,白首人间今古。又惊绝、五更一句。道是流离蜀天子,甚当初、一似吴儿语。臣再拜,泪如雨。画堂客馆真无数。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谁不愿封侯万户?寂寞江南轮四角,问长安、道上无人住?啼尽血,向谁诉?”等等。所以况周颐说:“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意态略似坡公。”(《蕙风词话》)
语言
语言上,他的词不受规范的制约,以散文章法、句法入词,不事藻饰。如:“那看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柳梢青·春感》);又如:“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永遇乐·壁月初晴》)。这些词的语言自然平实,亲切灵巧。此外,江西遗民词还有一定的口语化特征,不避俚语、俗语。如刘辰翁《摸鱼儿·甲午送春》:“又非他、今年晴少,海棠也恁空过。清赢欲与花同梦,不似蝶深深卧。春怜我。我又自、怜伊不见侬赓和。已无可奈。但愁满清漳,君归何处,无泪与君堕。春去也,尚欲留春可可。问公一醉能颇。钟情剩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休阿那。阿那看、荒荒得似江南么。老夫婆娑。问篱下闲花,残红有在,容我更簪朵。”语言上熔炼了“休阿那”“阿那香”“慌慌得似江南么”“老夫婆娑”等大量俚语、俗语。
诗
刘辰翁的诗歌取得较高的成就,1987年版《刘辰翁集》有203首诗歌,包括《四景诗》157首和古近体诗46首。刘辰翁的诗歌题材较广泛包括抒怀、咏史、写景、赠答和题画等,诗歌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一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他的诗歌一方面摄取了宋诗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具有江西诗派清刚峭拔的风骨,另一方面又汲取了唐诗的风神远韵,以清幽之语写怀恋故国的深情,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他看到宋末学习晚唐诗的弊端,吟花弄草,气格狭小卑弱,而宋末江西诗派的诗则推敲文字技巧,缺少情感色彩,所以他在创作中力避其失,“尽扫江湖晚唐锢习之陋”,由此可见刘辰翁的诗歌创作对宋末诗歌具有总结作用。刘辰翁以自己深厚的学识、对唐宋诗人艺术的独到深刻的理解和对诗歌技艺纯熟的掌握,为“诗之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个别篇章如《春晴》写“江柳长天草色齐,新晴何物不芳菲;无因化作千蝴蝶,西蜀东吴款款归”,稍具情韵,兼含寄托。他在《陈生诗序》中曾认为诗歌题材原很广泛,触景感怀,无不可以成吟,又指出“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随事纪实,是称名家”(《须溪集》),但自己却没能做到。
散文
明人宋濂在《黄文献公文集·金华黄文献公文集序》中评价宋末散文创作情况时说:“近代自宝庆之后,文弊滋极,陈腐之言是袭。前人未发者,则不能启一喙。精魂沦亡,气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泛绪风,文果何在乎?”可见宋濂认为宋末文坛靡弱无力没有创新气格。元人袁桷也总结宋末文坛的文学受理学牵制的弊端:“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刘辰翁散文共249篇,多有为而发,感慨至深。 他的散文在宋末乃至整个宋代都是别具一格:文思跳跃,充满想象;笔触放荡,不遵规矩;思维百般变幻而莫测其旨,语句断续钩棘而不知其意;熔铸经典,用典繁密,用词辟涩。
文学批评
刘辰翁还是文学批评家,批点评选古人诗文有10种之多。他的文学评点,种类繁多,涉及到诗歌、散文、小说、词等多种文学体裁。刘辰翁不囿于传统功利性的文学评点方式,立足于文学本体,从艺术审美角度出发评点持诸家,见解卓著,在文学评点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刘辰翁的出现,才使诗文评点摆脱了为科举而设的目的,而专以文学批评的标准来进行审视和判断。“宋末元初的刘辰翁。以全副精神。从事评点。则逐渐摆脱科举。专以文学论工拙。” 从这层意义上说。刘辰翁在中国文学评点史上处于重要的转折地位,他使评点从实用功利的局限中转向了艺术的广阔天地,也回归了文学的本位,他无疑在文学评点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评点大师”。
他在诗歌评点中,一般不注意创作背景,也不理会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更极少去涉及诗歌外围问题的考证,字词的训诂和典故的诊释他也较少顾及,他对诗歌的评点完全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或从诗体的起源和发展来批评,或从章法结构,或从风格特色,或从表现手法,或从诗歌的立意和主旨,或从实词、虚词的用法,不一而足。总之,其诗歌评点立足于诗歌本体,细论用字造句的奥妙,剖析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综合品赏诗歌的内容、风格、造境和修辞的技巧。刘辰翁所选择评点的散文也与一般辅助科举考试的入门书不同,而不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色彩,从其评点的对象《大戴礼记》《越绝书》《阴符经》《老子》《列子》等中可以看出其评点完全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决定取舍,是一种纯粹的无功利目的的文学评点。
他所评点的诗人有李白、杜甫、陈子昂、张九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储光羲、常建、柳宗元、陶翰、戴叔伦、韩愈、孟郊、李贺、沈千运、王建、孟云卿、张继、崔颢、张籍、张谓、卢全、裴迪、郎士元、卢纶、刘商、杨衡、王绍、贺知章、高适、岑参、武元衡、刘长卿、王之涣、贾岛、姚合、骆宾王、杜审言、苏颧、杜牧、钱起、卢象、司空曙、崔涂、皇甫曾、李澄。凡是在唐诗史上有特色的诗人,都进入了他批点评骘的视野。 评点王维、杜甫、陆游等人的作品,时有中肯之处。但他喜欢标新立异,常常失之尖刻和琐屑。尤其评杜诗每每舍其大而求其细。对同时代人汪元量的诗作,亦有批点评选。其词学批评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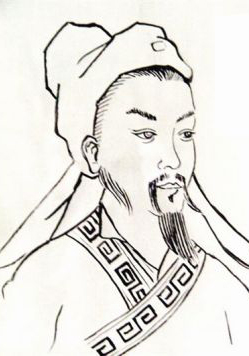 刘辰翁(1232年-1297年),字会孟,别号须溪。又自号须溪居士、须溪农、小耐,门生后人称须溪先生。庐陵灌溪(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梅塘乡小灌村)人。南宋末年爱国词人。
刘辰翁(1232年-1297年),字会孟,别号须溪。又自号须溪居士、须溪农、小耐,门生后人称须溪先生。庐陵灌溪(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梅塘乡小灌村)人。南宋末年爱国词人。